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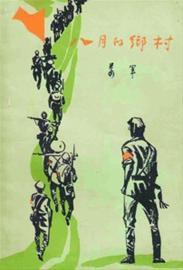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九一八”国难文学,迄今仍被湮没在历史中。它们是中国现代国难的历史活化石,但却没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成为历史文学之殇。打捞国难文学的活化石,彰显其特有的精神与历史价值,这在当下显得极为重要。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翔牵头启动了一项研究课题——《“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今年年初,该课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6月11日,高翔接受记者访问,他说:“我们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造‘国家记忆’。 ”
张恨水写出第一部国难小说
一个来自东北的在南京读书的大学生热衷于到戏苑捧角,后来因为“九一八”事件爆发,家中经济来源断绝,那个角不再理他。精神失落的大学生终于醒悟,毅然投军抗日。
——张恨水《九月十八》
普通读者认识张恨水,大多是因为他所写的通俗小说。鲜为人知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张恨水曾创作了大量国难小说,其数量之多、艺术之上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比肩。
“‘国难小说’这一特定文体的提出,最早就出现在张恨水笔下。 ”高翔说,张恨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便创作出版了一部国难小说集,取名《弯弓集》。“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还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爪子,殊亦有可念者也’。 ”根据高翔的研究,这段话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国难小说”一词的最早出处。
“九一八”不是东北一隅的劫难,而是全中国的劫难,早在80年前,这一认知便深植在国人心中。因此,当张恨水倡导“国难文学”写作后,一大批作家纷纷加入此行列,其中有顾明道、汪优游、程瞻庐等通俗小说作家,形成了独特的国难小说创作群和国难文学创作潮。
高翔告诉记者:“我们所承担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课题中的‘国难’一词,源于历史,但并不是对历史概念的简单借用。 ”以往,针对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的研究,大多重于言说当中的爱国精神与反抗品格。高翔认为,此类研究当然不可缺少,但同时,也要关注民众对殖民地苦难生活的承受,“这也许更符合多数国民生活的情状。这种视角的转换,将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 ”因此,在他看来,研究“九一八”国难文学,既要有对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深入挖掘,同时也应包含对国民性弱点和历史复杂性的认知和回归。
在课题论证阶段,高翔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对大量史料文献进行严谨梳理与分析,将“九一八”国难文学这一概念界定为既包括表现1931年9月18日日本炮轰东北军北大营、侵占沈阳城这一事件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基于“九一八”事变影响下的反映东北地区乃至中国民众国难生活的作品。他说:“我们认为,通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反映‘九一八’国难的文学文本,都可称为‘九一八’国难文学。 ”
大量文字仍沉睡在历史故纸堆中
在抗日前线,将士们顽强抵抗,不惜流血牺牲。而在抗战后方,银行职员何少爷却谎称救国会开会,跑去与舞女蜜丝洪相会取乐。他认为,抗日是庸人自扰,是傻瓜,只要住在租界,安分守己,就很安全。而事实是,何少爷家被日军炸成一片瓦砾,父亲和妻女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何少爷惊醒了,他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立志杀敌报国。
——蔡楚生 《第七个 “九一八”》
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9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新发现的蔡楚生的三幕抗日广播剧〈第七个 “九一八”〉》(作者刘家思、刘璨)。文中透露,蔡楚生是在1937年9月18日连续28个小时未眠写就了这个剧本,全剧共2万多字。
高翔认为,从目前可见的史料来看,“九一八”国难文学不仅是当时文坛的重要创作取向和价值标准,而且显示出庞大而触目的文学文本阵容,具有鲜明的文献学意义和珍藏价值,因此,“进一步保存、挖掘、整理和集成,是当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 ”
“国人对‘九一八’国难有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但是,对‘九一八’国难文学却缺少自觉的认知。学术界对当时作家也包括众多普通人对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提示中国民众奋起抗争的历史事件的文学书写,没有进行系统整理的理性意念和自觉行动,导致这些充满血泪与悲剧意识的文字,至今还大量沉睡在历史故纸堆中没有得到发掘。也由于时代的、社会的和技术的各种原因,许多宝贵的原始资料遭到破坏或佚失。 ”为此,高翔强调,对“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的整理,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抢救性工作。
同时,“‘九一八’国难文学研究还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宗旨是锻造对国难文学的文化层面的记忆,进而实现文化的认同。 ”高翔提醒说,对文化记忆进行“再造”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詹姆斯·扬曾说,对于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没有一个宏观的文化关怀,只是将南京大屠杀当做自己民族低层面的集体记忆’。很明显,他认为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还停留在情绪的、简单的、原生态的记忆。现在看来,我们对 ‘九一八’国难的记忆同样如此。因此,当我们对‘九一八’国难文学进行整理时,很大程度上是在推动一种‘文化再造’。 ”
失去了国难记忆也就失去了民族记忆
皮匠耿大在归家途中被日军抓捕,被逼为将要走进这条小巷的人挖掘 “死人坑”。日军将走入小巷的中国人逐一杀死,并头脚倒立埋在耿大挖就的坑中,双腿呈V形露出地面。目睹着同胞的逐一被杀,想到瞬间自己也将呈V形埋入坑中,耿大终于反抗了。
——罗烽《第七个坑》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开始,那么,‘九一八’国难文学便是对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叙事。”高翔认为,从罗烽的《第七个坑》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亡国亡族苦难的书写,意在告诉人们,民族生存的唯一道路不是苟安求活,而是义无反顾的抗争。
苦难是“九一八”事变带给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难以磨平的烙印,在苦难的背后,还有不屈的抗争。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可遗忘的历史,“九一八”国难文学正是民族历史生存的活化石。
“正是我们的先辈以文学的形式留下了大量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国难的记忆,因此可以说,这种记忆与历史一样,是有无可替代性的。这些文本积淀着民族的集体的记忆,失去它们,也就失去了民族、失去了集体。民族认同的文学史资源的遗忘,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致命摧残。因此,对这种文学进行抢救是责无旁贷的。 ”高翔说。
《生死场》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八月的乡村》是萧军所著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萧军的早期代表作。
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收录了短篇小说20篇,中篇小说4篇。(记者 王研)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